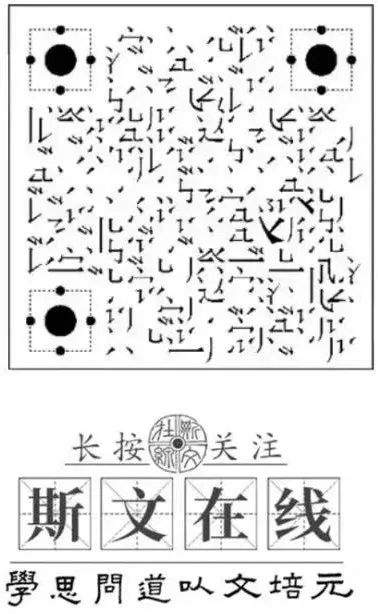猎U者 戴伊璇 | “填词”的离场——由民国词话之演变管窥当代词学萌芽
发布日期:2024-10-21 13:38 点击次数: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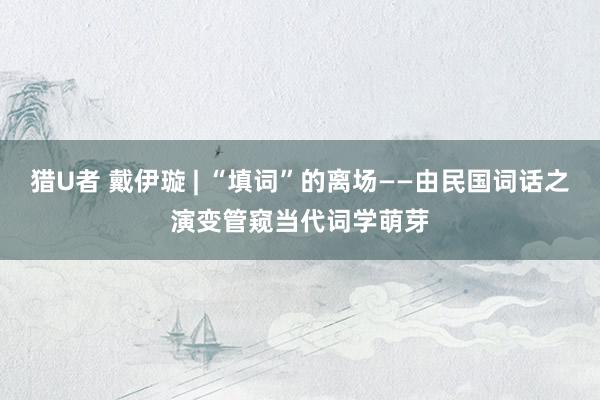
 猎U者
猎U者
一、绪论
当代词学的提拔平方被以为在20世纪30年代,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讨论词学之商榷》一文,这篇具有独创意思的论文被视为“当代词学出身的一篇宣言”,从此“词学”被纳入了一个与传统有别的清新学术体系中,有了明晰的界说与明确的讨论范畴。但当代词学的出身并非经由《讨论词学之商榷》一蹴而就,而是传统词学在近代以来的政局变化、社会想潮、熏陶轨制、出书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的势必走向。
猎U者
在这个走向中,创作论动作词学表面中的挫折组成部分,其演变尤其值得被关注。传统词学中,表面建构与审好意思阐释的最终主义是为了领导创作实践,即以民国之前的清代词坛为例,不管浙西派或是常州派,其词学主张都是为了在不同的政事配景与文化环境下,更全面地针对填词创作成立价值导向与审好意思范式,简而言之,是为了恢复“为何填词”“何如填词”“何如填好词”等一系列创作论问题。而在近代社会与文化遭到了当代性的全面冲击之后,如学者所说:“五四畅通以后,‘填词’的身分在淡化,而‘讨论’的身分在逐步强化,进而酿成了具有当代学科意思的‘词学’。”或者说,当代词学萌芽的进程,同期亦然“填词”的表面比重逐步减少的进程。
最能完好体现这个脱离进程的文本载体是民国词话,词话至民国也曾是极其锻练的文学批评口头,词话作家维合手传统词学的讨论阶梯与法式,同期也承载了鼓吹词学转型的重负。本文防卫到,民国词话的本色与阵势,在这个转型期中弥远方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进程中,尤其是“填词”的分离,使得民国中后期词学文本发生了显耀的变化。而“填词”的退场相同阅历了一个庞杂复杂的过渡期,并不是“填词创作沉沦了,当代词学就成立起来了”这么简略的因果逻辑。民国虽然时候不长,但囊括三代词东谈主,每一代词东谈主都有完全不同的熏陶配景和身份明白,新旧文化的冲突,更导致他们对于“应该何如填词”“何如看待填词的沉沦”等等问题,有着人大不同的不雅念与作念法。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在民国词话中的反应,以及词话怎样奴隶“填词淡化”这个因素产生变化,从而检会当代词学演进中的萌芽情状。
二、民国词话中填词功能与学词阶梯的改造
晚清词坛以临桂词东谈主群体为首,这一词东谈主群体在晚清词坛的一系列词学举止不成以简略的文学举止目之,其挟裹的政当事人义与政事能量阻难小觑。他们的词学主张与举止在清末阿谁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被激勉,催生出了晚清词学创作的喜悦,从中产生了不少填词名家,诸如朱强村、况周颐、郑文焯、夏敬不雅、易孺等东谈主。民国初年由于南社的文学举止频繁,旧体诗词的创作也仍然活跃,如吴梅、王蕴章、庞树柏、陈匪石等东谈主都是民初词坛的后发先至。但跟着1915年前后新文化畅通兴起,1917年南社终结,旧体诗词的生涯空间渐趋局促,加之填词创作门坎较高,词体逐步退出主流文学的舞台。对这个问题最为敏锐的,恰是在清末民初词坛上活跃的这群词东谈主,他们是词事昌盛时期的过来东谈主,同期又在民国有着为时不短的词学举止,更为锐利地感知到了填词创作日渐式微的趋势,况周颐就说“乃至倚声小谈,即亦将成绝学,良可慨夫。”开端被从新谛视的,是填词一门的试验意思,也即是“为了什么而填词”。
(一)从新认定词体功能
晚清的临桂词东谈主群体是一个特殊时间造就的特殊群体,吴熊和先生总结该派的团聚是“基于倾向维新与究心词学的换取兴味”,是极为适合的。以王鹏运为代表东谈主物的临桂词东谈主群体,将常州词派的经世主张与词学创作糅合于一体,强调填词创作所承诺载的社会功能与政事意思,并藉由词学举止与政事举止的相反相成,振起晚清词坛。但插足民国纪元后,不管是帝制如故维新都成为了往时式,这群词东谈主不管出于主动如故被迫,都已远隔政事生活,致使被排斥在新时间之外,具体到填词上,他们信奉的那套经世致用的创作东张已与试验生活恼恨比好意思,因此对于填词创作在新时间新环境中还保留哪些价值功能的问题,与百姓词东谈主最为躬行,在他们的词话中被关注得最多。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能体现出词体价值明白转化的,是况周颐的《蕙风词话》。
况周颐动作临桂词东谈主群体的代表东谈主物之一,清澈地看到,在时间俗例的调度下高论词的社会功能已显得宽裕了,和常州词派的前东谈主不同,他在《蕙风词话》中并莫得肆力举高词的文学地位,而是直言“词于各体笔墨中,堪称末技”,但末技也有末技的存在价值,《蕙风词话》从新界定填词创作之于个东谈主的价值与意思曰:“吾特性为词所查验,与冷凌示寂事,日以火去蛾中。”填词不再是为了“托志帏房,眷怀君国”,而是为了“养成不入时之特性”,是摒弃冷凌示寂事、自我高蹈的精神追求,能够亦然旧词东谈主与时间激流相挣扎的惟一阶梯,也即是“夫词者,正人为己之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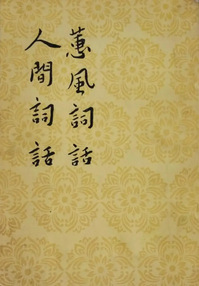
况周颐更进一步将填词总结为儒家士医生个东谈主的修身之谈,《蕙风词话》的创作论中强调襟抱和特性,何为襟抱,他举了一个例子:
宋王沂公之言曰:“平生志不在饱暖。”以梅诗谒吕文穆云:“雪中未问调羹事,先向百花头上开。”吴庄敏词《沁园春·咏梅》云:“虽虚林幽壑,数枝偏瘦,已存鼎鼐,少许微酸。松竹交盟,雪霜苦衷,断是平生不愿寒。”二公襟抱政复换取,少许微酸,即调羹苦衷。不志饱暖,为有不愿寒者在耳。
他招供的“襟抱”是某种无法被梗阻生活所消磨掉的高远志向,亦然不向粗暴试验折腰的倔强,所谓“贫贱不成移”者也。那么何为“特性”?《蕙风词话》在论程文简时,评其“特性厚”,评刘文靖词“以特性朴厚”胜,又引王半塘论《樵庵词》之言“朴厚深醇中有真趣飘溢,是特性语,无谈学气”,可见所谓特性,是儒家所追求的温煦敦厚之品格,而这种品格不是假惺惺的谈学气,是歌哭悲喜的东谈主生情状,是真趣。襟抱与特性与其说是填词的先决条件,不如说是况周颐藉由填词打造的一个想象的儒士形象,因此况周颐将填词精进的进程视作儒家的修身之谈,曰:
问:填词怎样乃有仪态?答:由养出;非由学出。问:怎样乃为有养?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始。问:清气怎样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复托根人间,甚且断井颓垣,乃至虐待为红雨,犹香。
善葆清气,出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蕙风词话》中填词一事所承载的“言志”功能秉承的是传统儒家诗教的另一面,从批判试验总结修身养性,其中诚然有超然通脱,更多的如故遗世孤立的荒原与失落。这种填词功能论是传统士医生“树德、建功、立言”三大想象都摧毁之后,儒家“达则兼济六合,穷则独善其身”不雅点在词学上的不雅照。
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民国词坛的分量级词话,也不错说是常州词派表面构建的收官之作,主张弱化词的“言志”的社会功能,转而强调词对个情面志的表达作用,不错推断晚清的词学创作论也曾濒临无法适合新的时间要求,亟需自我休养的逆境。
(二)探索新的学词旅途
事实上,民国时期除了少数百姓词东谈主外,不管是词话也好词学论著也好,也曾鲜少有作家关注填词的试验意思,更多的防卫力放在怎样支援这门末技上。如果说况周颐《蕙风词话》着意于改写填词在功能层面上的尺度,那么更多词东谈主则是介意填词技术上的门坎。20年代后晚清词东谈主渐次离世,懂填词的东谈主越来越少,老一辈词家感受到了词学逐步被主流文学所充军的孤苦孤身一人,如蒋兆兰在《词说》自序中如斯感叹谈:
嘅自清命既讫,谈丧文敝,二十年来,先民尽矣。专有强村、蕙风,喁于海上,乐则为天宝霓裳,忧则为殷遗麦秀,是可伤已。乃今岁初秋,蕙风奄逝,吾谈亦孤。
因此重振词学的但愿委用在后学身上,他在自序中先容《词说》的创作缘由时说:“诸生以老马识途,常常从问词法,兼求词话,奉为准则。”可是“又虑晚世学者根砥不具,则枝杈不荣。”事实上,向蒋兆兰问学的吴梅、陈去病等东谈主,都是旧学底蕴深厚的文东谈主,这里的“晚世学者”更多是指收受新型熏陶成长起来、对旧学较目生的后生学子。
晚清词坛的审好意思风俗简略言之,是选涩调、讲四声、重故实、真金不怕火字面,珍视《梦窗词》,这种俗例在民国初年演至顶峰,所谓“晚世学梦窗者几半六合”,但这种创作审好意思对创作家的学力要求极高,绝大多数只是是一步一趋,作品也多生硬砥砺、晦涩饾饤。另一方面,口语文兴起,全球马上收受了这种平凡明白的行文方式,同期跟着文言文和旧体诗词逐步离开日常生活,不要说填词,致使清醒词调的基本格律、明白词中典故的东谈主都越来越少,词逐步变成一门远隔试验的传统文学身手,面对这么一种“杨春白雪”的逆境,倚声家们运行探究怎样裁减填词的门坎,为这门绝学保留一线但愿。
当先是对清末民初的词坛俗例进行反想,主如果反想“梦窗热”影响下过于强调技法和学问的创作倾向,尤其是针对“严守四声”和“堆砌典故”这两个要津。
早在20年代的词话中就已有清百姓词家试图对“梦窗热”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生死继绝,宣雨苍在《词谰》中明确反对同期代词东谈主吹捧梦窗、以涩为尚的俗例,并以朱强村的词为例谈堆砌砥砺的毛病:
近日词家争相祖述(吴文英),饾饤写来,几不谚语。尝见今世奉为词伯者有传句云:“窣波钟动,归去连钱,蜻蛉催泛。”可谓涩矣,然“窣波”何不径用“佛楼”?“连钱”何不径用“花骢”?“蜻蛉”何不径用扁舟?使读者不错豁然意爽,仍未见其稍倍词旨,必欲强借名词,逐一帖括,好为其难,毋论矣。乃并其强借之名词,不求甚解,是诚大可怪也。试为正之,如“窣堵波”为梵语,译即塔也。塔非藏钟之地,钟则别有钟楼。而“窣堵波”一句梵语,尤断不成截去“堵”字,但用“窣波”,致不谚语。即彼或曾见前东谈主有误者,以为是有所本,而不知为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也。彼执词坛牛耳者传作且如斯,世之依草附木,自号倚声家,更可知矣。
“窣波钟动,归去连钱,蜻蛉催泛”三句出自朱强村《烛影摇红·月夜泛舟里湖,遍串六桥并丁家山而归,山椒一园,歌饱读彻曙》,作家胜利将锋芒指向“梦窗热”的“始作俑者”朱强村,以为词坛名家犹如斯,何况学力普通的一版词东谈主呢。夏敬不雅也说:“今之学梦窗者,但能学其涩,而不成知其活。”遗老尚且如斯,略微的词家则更普随地意志到到了其中的毛病,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熏陶怎样填词,就提示曰:“近东谈主喜学梦窗,通常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此病甚多,学者宜寄望。”很彰着,有教训的词家都意志到了学梦窗之“质实”与“涩”是需要学力门坎的,并不适应当下的学词者动作心慕笔追的预备。
“守四声”亦然相同的情况,《柯亭词论》以为“守四声”是填词的进阶课程,曰:
词守四声,乃进一步作法,亦临了一步作法。填词须不感古板之苦,方能轻车熟路。故初学填词,实无守四声之必要。不然辞意不成领会,律虽叶而文不工,似此填词,又何足贵。
龙榆生也以为选涩调、守四声会影响词中情志的表达,他曰:“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千里埋。”蔡嵩云与龙榆生均是词学熏陶家,执教于高校,因而愈加能体会到严守四声给初学词者带来的禁闭。
其次是探索更适应初学者的学词旅途。周济提议的“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一直是常州词派创作论中教科书级别的学词旅途,其容身点在于南宋词的立意、笔法、结构都是有径可取的,其艺术技巧不错靠揣摩、师法进行学习,但在词学濒临中绝时,词学家运行反想这条旅途是否还适应当下的学词者。
夏敬不雅在《〈蕙风词话〉诠评》中明确批评这种旅途是倒置因果说:“止庵谓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乃倒果为因之说,无是理也。”《诠评》更进一步反对初学者从南宋脱手,先以常州词派两位代表东谈主物张惠言与周济为例,入木三分指出常州词派表面强势而创作颓势的要津场所,借此闪现为何不可学南宋词,曰:“张皋文、周止庵辈尊体之说出,词体乃大。其所自作,仍不成如其所说者,则先从南宋词脱手之故也。”不可不谓果敢。
周济的“四家逆溯之法”耐久以来被招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部分词东谈主以为小令最难填,应该从长调运行学习怎样铺叙、构架、声律等基本技巧,而南宋词以长调为主,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可是由长调初学,所需要学习的格律知识、笔法技巧、典故史实等颇费功夫,需要较为塌实的文史基础。
因此《词说》主张学词之前要先学作诗,曰:
初学作词当从诗脱手,盖未有五七言不成成句,而能作长短句者也。词中小令,收处贵含蓄,贵神速,于诗之七绝最近。慢词贵铺叙,贵粗率,贵海潮飘荡,贵挫折聚散,尤与歌行动近。其他四五七言偶句,则近于律诗。是故能诗者,学词必一本万利。
因为诗中五言、七言律句,都是词中常见的,先熟习律诗的声律神情,遣意造句,了解旧体诗词的创作礼貌。第二步才是填词,“初学作词,如才力不允,或先从小令脱手”,因为有学诗的基础在前,如果天分高的话,易得名隽之句,接着才学填慢词中格律较宽、拘谨较少的词调,临了才是精研词律声韵,尝试孤调、僻调。这么的学词法昭着是针对莫得旧学根砥的新学东谈主而发,从作诗运行补旧学的基础课。

三、新型词学熏陶影响下词话的功能分化
不管是从新检会填词的功能,如故探索“逆溯之法”除外的学词阶梯,大多仍属于常州词派里面的创作论修正,对于这种修正最为积极的大多是清百姓词东谈主,他们虽然能感知到填词创作的式微,但并不胜利面对新型熏陶和后生学生。而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东谈主生阅历和举止在民国的这一辈词东谈主,比喻刘永济、吴梅、陈匪石等东谈主,他们与晚清名家多有师生之谊,旧学根柢深厚,兼擅倚声,在20年代后插足高校,成为身膂力行熏陶新模式的一代学者,他们率先创立的讲稿式词话,随意促进了民国词话的“填词”离场。
为了适合新型熏陶下的施教需求,“低门坎学词法”运行代替从前以技法风骨笔力为中心的创作论,这种替代与转化体现时阵势上,则是条件明晰的知识结构代替了随性零碎的片断式文本。传统词话创作的体例多半是闲谈杂文式的随意表达,其本色包罗万象,创作论范畴论欣赏论十足包含在内,全凭作家喜好解放发达,不仅费力系统性框架,理敷汇报也比较抽象。可是跟着词学动作一门当代学科走入课堂,传统词学家著述的预备群体变了,面向的是不了解词的学生群体,同期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带来了高级熏陶中的学科细分,具体到词学一门,“词学”这个见地也细分为多种课程,以1928至1929学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例,共有四门触及词学的课程,分别是“词学”“词曲通论”“中国词史”“众人词”,在以具体的教学预备为主导的课程体系中,传统词话天然无法匹配新出现的词学熏陶需求。
因此,插足了一个词话体例的转型期。以身在高校的几位词学家的词学讲稿为例,体例约莫不错分为两类,一类偏重词学教材与课本,主要以传授词学知识为预备,另一种仍是传统词话,充满兴会所至,信笔拈来的个东谈主感悟,不外二者之间并非奴颜媚骨,词学熏陶尚在起步阶段,讲稿莫得现成的范式尺度,加上大部分讲课熏陶都深得旧学教学,因此难免将词话的笔调带入讲稿的撰写之中,使得这些讲稿类词话大多介于由词话向论著过渡的一个朦胧的阵势中。但在这个略显庞杂的转型期里,有一个特征诟谇常彰着的,即是“填词基础”与“词学讨论”被区分开了,这里所说的区分,不仅包含某孤立文本中两种本色的区分,也包含不同著述层面上的区分。
(一)讲稿词话中“填词”与“词学”的区分
先来看吞并文本下的“填词”与“词学”的区别,这主要体现时动作课程讲稿使用的词话之中。词学熏陶家在20年代也曾防卫到了跟着学科愈来愈细,怎样填词与词学讨论也逐步兵分两路的试验。寿鑈在讲课所用的《词学轻佻》中曰:“词东谈主无意工于论词,工于论词者,其词又无意工。”在高校教学的需求下,许多教材也曾在“学词”和“词学”上作念了区分。比喻《海绡说词》是陈洵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稿,主要本色分为通论和名家词作赏析两部分,通论主要谈及填词的一些基本教诲,比喻“师周吴”“志学”“严律”等,赏析部分包含《梦窗词》《片玉词》《稼轩词》三家词的详解。可见虽然纯用传统词话的体例,但将创作与欣赏稍作了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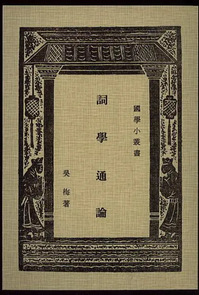
吴梅的《词学通论》又更进一层。《词学通论》是吴梅于1922年秋至1927年春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讲课课本,全书分为“绪论”“论平仄四声”“论韵”“论音律”“作法”“概论”六部分,其中“概论”又分为“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章。“绪论”共10则,体例全依照传统词话而来,开篇首则即曰:“词之为学,意内言外。”然后谈词的起源与词体的特征,接着按序论词与诗、曲在创作中的区别,小令、中调、长调之区别的误区,词中调同名异者,填词的协律与用字发意,咏物词,是否需要严守四声,词之用韵,词之择题等,这个门径,其实即是学习填词行远自迩的一个旅途。是一个对于“怎样填词”的基本本色。绪论部分,雅致简要,真切浅出,与旧体词话无异。此背面绪论的逻辑上细分为几个章节,是偏重词学讨论的本色,突显条理,又添加表格与小目次,便于学生相识,兼顾讲课的需要。
456在线
又举例刘永济的《诵帚堪词论》上卷为“通论”,分为“名谊第一”“缘由第二”“宫调第三”“声韵第四”“风会第五”五个部分,下卷为“作法”,分红“总术第一”“取径第二”“赋情第三”“体物第四”“结构第五”“声采第六”“余论第七”。不丢脸出,与吴梅的《词学通论》相似,《诵帚堪词论》上卷主如果词学知识传授的部分,下卷紧扣词旨与词法的,属于创作表面叙述。
因为是用词话阵势写成的讲稿,又常动作词话发表,姑且可称为“讲稿词话”,这种新兴词话当先改造了词学创作论的内涵,使“离场”更为胜利,使批评论析更为具体真切。天然,在过渡期里,这些讲稿并非一刀切式的奴颜媚骨,部分敷陈并不成完全割裂“填词”和“词学”两者。只可说大部分作家意志到了传统词话本人的无序杂沓也与高校熏陶的专业化、学术化的趋向以火去蛾中,并特地志地在讲稿中将二者进行了区分。
(二)动作一门孤立身手的“填词”
“填词”与“词学”的分离并不单是发生在高校词学课程之中,既然讲稿也曾在区分二者,“填词”进而从讲稿孤立出去,出现了围绕“怎样零基础填词”的一系列学词用具书。这类用具书的体例介于词话和讲稿之间,相同可视为民国词话朦胧转型情状的某个横截面。“填词法”文章兴起的紧要原因天然如故出于词学熏陶的需求,许多词学课程都包含创作的检会,如刘毓盘的考试办法即是“唯有你填一首词即是。”冒广生也说:“庠序之子非学词无以卒业”,可见会写词亦然那时课堂上的一种刚性需求。另一层原因则是出书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强烈的买卖化竞争,诸如大东书局、天下书局、崇新书局等以民营本钱为主的中小出书机构,在买卖运作方面都颠倒积极机动,典籍筹备与履行都以读者的需求为中心,其中也相投了词学熏陶的需求。千般“零基础填词法”应时而生,成为民国词坛沿途特别的表象,举例吴莽汉《词学初桄》、傅汝楫《最浅学词法》、顾宪融《无师自通填词百法》、刘坡公《学词百法》等。这批用具书的出现,代表填词成为了一门传统身手,完全告别“经世致用”和“词史”这些创作论见地,有以下几个特色。
当先是栽培性强,面向普罗全球,从富饶招引力的书名就能看出,这些书是供初学填词者使用的,并且有诸如“无师自通”“最浅”这一类略显夸张的宣传标题,旨在招引完全不曾战役填词的生人。《无师自通填词百法》的《自序》中谈:“兹编之辑,即为初学各位作向导,故陈义不尚高妙,遣意务求浅陋”,一语谈出这类发蒙词话的卖点。
其次这类填词法体例新颖,当先通过安排目次章节,使得全文条理明晰,具备系统学习的便利。为了初学者探究,各书一般都会触及词的发祥、词体与其他诗歌文学的区别、宫调与四声五音的基础知识、词律与词韵的用具书与检索法式、历代词东谈主词派点评、词调范式(或词谱)这些本色。并且在结构安排上,不仅分了章节,在大标题下还有细分的小标题,不可谓不精细,并且检索简便,初学填词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作家都提前意想了,令读者不错将其视作词学的百科全书,有问题唯有对照臆测条件,就不错寻得解答。
需要闪现的是,虽然这些填词法在体例上有所翻新,但内涵并未脱离传统词话的范畴,文本中词话与词学论著之间的界限十分朦胧,以《词学初桄》为例,全书的主体部分其实是师法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的词谱,不错无论,前边前言分16个部分,如果拿掉落款,也即是普通的16则词话汉典。再如《无师自通学词百法》,上卷论词旨词法,下卷月旦历代词东谈主,虽然都单独附上“xx法”的标题,本色与传统词话别无二致。在这少许上,“填词法”与诸如《词学ABC》《词学知识》这种词学论著阵势的通识读物有着显耀区别,后者是以论文体例或教材阵势章节组成的著述。
(三)剥离“填词”后的词话
既然“填词”一门也曾另立派别,那么抛独创作论的传统词话,天然在本色上也发生了要点的回荡,一方面是减少抽象零碎的表面建构,另一方面是将要点转向怎样阐释、赏析作品,这少许在动作教学讲稿的词话中尤其彰着。
以《海绡说词》为例,虽然通论部分是讲授填词基础,但主体部分是“说词”,试举说《霜叶飞》(断烟离绪)一例:
海绡翁曰:起七字,已将“纵玉勒”以下摄起在句前。“斜阳”六字,模糊表象。“半壶”至“风雨”十四字,水长船高。以下五句,上二句隆起凄惨,下三句平放和婉。“彩扇”属“蛮素”,“倦梦”属“寒蝉”。徒闻寒蝉,不见蛮素,但仿佛其歌扇耳,今则更成倦梦,故曰“不知”。两句神理,结成一派,所谓“关切事”者如斯。换头于没趣中寻出消遣,“断阕慵赋”,则仍是消遣不得。“残蛩”对上“寒蝉”,又换一境。盖蛮素既去,则事事都嫌矣。收句与“聊对旧节”一样意思,见在如斯,畴昔可知。极感怆,却极闲冷,想见觉翁胸次。
《海绡说词》的主体部分均如斯例,行将一首词休止,细究字句与其中布局关联,梦窗与清真词档次丰富,前后勾连,对于初学者来说的确难懂,陈洵我方也说:“吴词之玄幻,简直急索解东谈主不得。”这就给不熟习旧体诗词的学生带了不小的审好意思禁闭,但《海绡说词》不仅在章法结构上说得颠倒精细,并且对于用字下语也评点得深到,首尾照看,勾连阕,有种作品串讲的意思,大不同于传统词话触及作品的片言一字而不易得要领,也可说是兼顾词学熏陶的一种翻新,这番精细解读之下,整首词的词意、笔法、结构、艺术特色都明晰无疑。

除了本色方面向欣赏歪斜,体例上也为简便读者进行了改良,如陈匪石的《宋词举》,此书集词选、词话于一身,先录作家小传与词集版块源流,再集前代名家评述,再录词作,词作中标出韵位,每首词后有“校记”、“考律”、“论词”三科,“校记”主要纪录各个版块中的异文。“考律”一栏,一般先溯词调发祥、词牌别称,再凭证此调字数析其数种阵势,细析每一体的平仄、句法区别。“论词”是词作赏析,极为抽象透澈,短则四、五百字,长至一、二千字,一字一句分析句法、字面、结构之要领,另掺杂词本事的记叙与对词境的体悟,偶尔还会与其他词东谈主或词作比较较,优劣互见。此三科是传统词话批评中常见的论词主题,但这些主题散见于旧体词话中时,常常是一鳞半瓜,让初学者摸不着路途,通常“知句而不知遍,知遍而不知篇”,陈匪石评价前东谈主词话,也委婉指出张炎、沈寄父、周济、陈廷焯、况周颐等东谈主的词话“咸有伦脊”。
《宋词举》中别出机杼地将这几个主题以词动作中心衔接起来,简直囊括了解一首词所需要的全部因素,其抽象进程,民国再无词选能出其右,唐圭璋评价此书:“自来选词者,无举词详析之例,有之自匪石先生始。”可见其独创之功。

熏陶者的对面是学生,如果说老一辈词学家通过多方改良传统词话使其适合新时间的要求,并为后东谈主翻开了词学欣赏文体的先河。那么动作收受者的晚辈后学,在词话中则更多地体现出当代词学讨论的端倪。
举例唐圭璋先生的《梦桐室词话》,这部词话是他整理辑校《全宋词》的副居品,绝大部安分容为词学文件勘考,且多属于宋词的文件范畴,约莫可分为作品辑佚、作家考辨、版块溯源、订误辨伪等几大类,其中发明最多的是辨伪条件,如“明东谈主伪作陆放翁妻词”“《学海类编》中所收之伪词话”,又多有对宋词作家的考辨订误,如更正误署杨妹子而实为张抡之作的《题马远松院鸣琴图》,考辨鲁仲逸即孔方平,一首词作,一位词家,皆辨析有据,发覆无疑。有时通常是作品辨伪与作家考定并行,在指出周邦彦的《水调歌头》“中秋寄李伯纪不雅文”一阕是伪作后,又找出此词着实作家为何大圭,所谓“既明其伪,复补其缺,是亦快事也”。在辨析《词林纪事》所载的文天祥《南楼令》时,唐圭璋惊奇谈:“乃知后东谈主援用前书,通常不及据,非复校原书不可。”这简直个中东谈主甘苦之言,会心之得,可引以为校勘学不刊之教训谈。因为词话所固有的体例特色,《梦桐室词话》莫得展示繁琐的考辨进程和数据罗列,但相同驾驭词话片言只字的笔法,片言一字论析明晰,使读者有陈迹可寻,有依据可凭。
《梦桐室词话》的文件学主旨纯正,本色蚁集而丰富,这在词话发展进程中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本色与阵势的打破,本不错用文件文章阵势来盘考的问题,却给与了更为轻便简捷的词话阵势来表达,一来是将平日校勘点滴所得作一番随录式笔札,二来是大型总集未便揽入的文件稽考本色自当整理,另行注销,对于当代词学讨论的辑佚之学有挫折意思。
相同富饶代表性的是萧涤非先生的《读词星语》,该词话发表于1929年的《清华周刊》,是萧先生在清华就读期间的学词心得。全文连“小序”共66则,每则前以词东谈主姓名为标题,对词东谈主评价不着意于辩驳,而是着眼与词中佳句的出处与注解,“颇有为前东谈主所未发,亦间有与旧说相补证者。”卓尔不群之处在于,不谈词旨,不涉词史,也无关声律与立场,单从文本字面锲入,探求词句来源,专心于名句的出处,这是《读词星语》的一大特色。尤其深细妥帖的是论周清真《六丑》名句:
好意思成《六丑》蔷薇谢后作词,时而说花,时而说东谈主,时而东谈主花并说,极变化浑成之妙。其“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轻翻柳陌”,则仍是说花,非说东谈主。《片玉词集注》引杜诗“神女落花钿”,失其旨矣。唐徐汇《蔷薇诗》云:“朝露洒时如濯锦,晚风飘处似遗钿。”词盖本此。全词“似牵衣待话,别情迷糊”,陈注缺,余按储光羲《蔷薇歌》云:“高处红须欲就手,低边绿刺已牵衣。”
其中体现了诗话的某种传统因素,即论者专注于文本的祖述与溯源。中国文学的语汇、字句、典故等等,历代流传,袭用变化,酿成既有祖述又有翻新的文学动态。“诸引文证,皆举先以后光,以示作家必有所祖述也。”所谓“文证”,即把原文出处揭示出来,“举先后光”本是诗文评注的挫折见地,亦然传统诗话文论广阔使用的法式,宋代以来,诗话流行,其中引诗摘句,溯其由来,更是不堪摆设。只不外词话晚出,专论亦少,尤其晚近以来,在崇论委用、杂谈佚事、标举立场的词话中,像《读词星语》这种幸免破碎,单纯专一于词句祖述的词话未始经见,因此显得特别而贵重。除此之外,《读词星语》擅长以诗证词解词,这需要论者的诗学功底,不仅是文件验证校勘之法式,亦然词体讨论的一大脱手处。《读词星语》打破前东谈主的词话范式与本色,留心词与诗的渊源干系, 既是陈旧诗学传统的讨论阶梯,亦然清新的词学法式。
师生相同沿用传统词话的体例,又各有侧重点与翻新之处,也涌现出词话这种传统文体在当代词学替代传统词学时所保留的另一种可能性。
四、余论
传统词话同期承载词旨、词法、词律、文件版块、填词技巧、创作立场、审好意思欣赏等多种词学式样,是一种大杂烩式的文体。跟着倚声创作在民国文学界的日渐没落,词话也运行发生变化。先是从表面修正的角度从新谛视“填词”的功能与价值,并反想晚清以来过分强调技巧学力的创作导向,这种变化还只是发生在词话的本色层面,但跟着词学熏陶成为高校熏陶课程的一部分,“填词”与“词学”分谈扬镳,创作论从词话的本色中逐步剥离开来,孤立成为一门传统国粹期间,这种分割体现时了词话体例的层面,词学讲稿与填词用具书是最能体现这种阵势上的变化的,剜去“填词”后,偏重科学系统的讨论论证主要由当代词学专著或论文承担,词话本色运行向批评欣赏的标的歪斜了。
以上是本文试图检会的民国词话中“填词”的离场进程,但历史的发展是充满复杂性与千般性的,“填词”的退场不成简略代表传统词学的末日,当代词学的肇兴也并非只是再行想潮而来,单一的端倪叙述虽然适应梳理历史发展的挫折陈迹,但也难以全面不雅照其间的细枝小节。
胡云翼在《词学ABC》中论其书主旨时说:“我毫不像那些遗老们,抱着‘收复中国固有文学之洪志’,来‘发达词学’的。”又说:“我这本书是‘词学’,不是‘学词’……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法式,并且顶点反对现时的咱们,还去填词。”这天然是一种难免顶点的不雅点,但也从中看出新派词学家“重解不重作”的一种集身形度,民国时期有许多类似立场的词话,作家主如果新后生学子,以欣赏月旦以及追溯词的历史为主要本色,但由于费力旧学根基,因此评价范围大多很局促,作家上主要关注唐五代与北宋词东谈主,文学上以短小但宽裕韵的小令为主,并且解词的技巧比较单一,无非是强调激情古道,天然有味。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新文学帽子下的词学中枢见地颠倒费事,无法从“意境说”或是“口语说”演出绎出更完好的表面学说,是以只可不休类似车轱辘话,是以许多新派学子的词话照搬王国维、胡适二东谈主的表面,致使胜利大段抄写,质料颠倒随意。
而围绕创作张开的传统词论则不一样,其中充满理性体悟与千般抽象见地,适应进行证据和二次解读,更能凭证试验创作的需求不休进行休养,生发出新的表面主张,这种“活的”词论的基础,在于不同期代不同作家不同文学想潮下创作实践的鬼出电入,是以即便“填词”退场,词学批评仍需要吸取传统词学中的见地,尤其是艺术阵势上的一些表达,比喻俞平伯《读词偶得》中广阔模仿常州词派的见地,呈现出更丰富高深的词学批评立场。而老一辈词东谈主一方面尽量适合新时间的要求,在传统词话的范式体例上进行了休养与翻新,这些新变成为当代词学酿成谈路上的基石,可是从词学立场而言,他们并莫得任凭“填词”的退场,而是但愿辅导后学藉由学习和欣赏从新总结填词创作,如陈匪石在《宋词举·叙》中说:“盖欲学者通古博今,由是而能读、能解,驯至于能作,悉衷大雅,毋入邪道。”《最浅学词法》虽然是用具书,其着作主义亦然出于“恐阅数十年,难免如高筑嵇琴,绝响东谈主间矣,心窃忧之。”在词学中绝之时所保合手的这份守先而待后的立场,为当代词学讨论注入了愿景的光彩。
(原载《词学》第4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23年6月版,注释从略)

【作家简介】
戴伊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讨论所助理讨论员,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讨论标的为词学、近代文学。在《词学》、《皆鲁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主编:朱生坚
剪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